1990年,我在《楹聯藝術發展十年》中,提出要擺脫前人的束縛,解放思想,講了下麵一段話:
當初的桃符,是在大門上畫荼和鬱壘兩個神像,後來變成左邊是“神荼”兩個字,右邊是“鬱壘”兩個字,用桃木板刻上的。這是什麼?我們為什麼不能將它叫做最早的對聯呢?
也許被當作異想天開的即興之言,這段話幾乎沒有任何反響,成了過耳之風。其實,提出這個觀點,我是經過思考的。

一
從神話中的荼與鬱壘,到門上的畫此二神像,出現桃符,這一事實,是普遍地被人們所接受的。
最早記載這一神話的,是《黃帝書》和《山海經》:
謹按《黃帝書》:上古之時,有荼與鬱壘昆弟二人,性能執鬼。度朔山上章桃樹下簡(檢)閩百鬼。無道理妄為人禍害(者),荼與鬱壘縛以葦索,執以食虎。於是,縣官常以臘(月)除夕飾桃人,重葦茭,畫虎於門,皆追效於前事,冀以衛凶也。(漢應劭《風俗通義·把典第八·桃梗葦茭畫虎》)
《山海經》曰:“北方有鬼國。”……《山海經》又曰,滄海之中,有度朔之山。上有大桃木,其屈蟠三千裏,其枝間東北曰鬼門,萬鬼所出入也。上有二神人,一曰神荼,一曰鬱壘,主閱領萬鬼。惡害之鬼,執以葦索以食虎。於是黃帝乃作禮以時驅之,立大桃人,門戶畫神茶鬱壘與虎,懸葦索以禦。(漢王充《論衡·訂鬼篇》)
王充所引,在今本《山海經》中不存。查《山海經》隻有相關的兩處:“鬼國在貳負之屍北”(海內北經);“大荒之中,有山名衡天,有先民之山,有桀木千裏”(大荒北經)。很難說它們與神荼、鬱壘有確定的關係,因為度朔山在“東海”(見《論衡·亂龍篇》)。王充所見的《山海經》想必是沒有被後人刪訂的一種本子,他的引文應該是可信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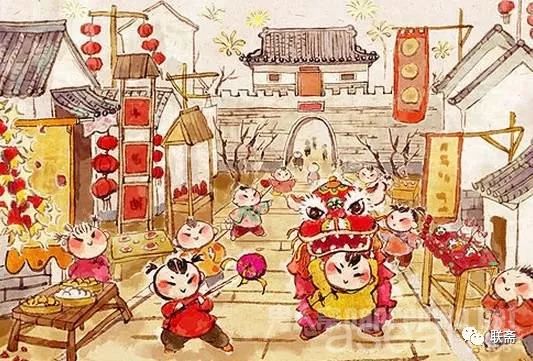
二
我們所感興趣的,並不是這個神話本身,而是它在民俗學中產生了什麼影響;我們尤其要注意的是,在驅鬼避邪這一原始思想支配之下,人們在門戶上除了“畫神荼鬱壘與虎”,還寫了什麼文字。
《新編連相搜神廣記·後集》在引用《山海經》上的神話之後,說道:
於是,黃帝法而象之,因立桃板於門戶,上畫神荼、鬱壘以禦凶鬼,此則桃板之製也。蓋其起自黃帝,故今世畫神像於板上,猶於其下書左神荼、右鬱壘,以元日置之門戶也。(轉引自《中國神話資料萃編》)
桃板是什麼?五代後蜀馬鑒《續事始》中“桃板”一條是這樣說的:
《玉燭寶典》曰:元日造桃板著戶,謂之仙木,以鬱林山桃,百鬼畏之,即今謂之桃符也。其上或書“神荼、鬱壘”之字。(見《說郛》卷十)
這裏所引的《玉燭寶典》,是隋杜台卿所撰。
從以上關於祧符上所書“左神荼、右鬱壘”文字的記載,我們不難看出,至晚到隋代,門戶上已經有了“神荼、鬱壘”這四個字了。

三
用對聯的獨立性、對稱性等基本特征,來考察古代門戶上的“神荼、鬱壘”,會出現什麼結果呢?
首先,這是以禦凶鬼、祈吉祥為目的的,有獨特的區別於其他文字的功能;它不需附加其他文字,就能給人以關於兩位神人的形象聯想,具有獨立的意義;它具有特定的時效性,即“元日置之門戶”,與春聯的作用完全相同。
其次,我們發現,“神”字本沒有,是後人加上的去的。“荼與鬱壘昆弟二人”隻能理解“荼和鬱壘兩兄弟”,不能理解為“荼與、鬱壘”(《中國神話傳說辭典》)。至於“下有二神,一名鬱,一名壘”(《漢學堂叢書》引《河圖括地圖》),則可能是訛誤所至,可以不去討論。
為什麼一定要在“荼”前加“神”呢? 道理很簡單,為了書寫的對稱性:大門上,一邊是兩個字“鬱壘”,另一邊是一個字“荼”,便破壞了中國人心目中的均衡對稱美。而加了這個“神”字,便使事情產生了質的飛躍,有意識地使這兩個神名,具有對仗的意義,這便進入了對聯的範疇。
由“荼”變成“神荼”.應該是漢代的事。漢代文獻引古文時,依前人用“荼與鬱壘”,如《風俗通義》引《黃帝書》;敘述古文時.則用“神荼鬱壘”,如《論衡》介紹《山海經》;詩文創作,一律用“神荼鬱壘”,如張衡《東京賦》:“度朔作梗,守以鬱壘;神荼副焉,對操索葦。”《論衡·亂龍篇》中,將“神荼”與“荼”同時使用,是不是更能說明在“荼”前加“神”就在漢代呢?
上古之人,有神茶、鬱壘者,昆弟二人.性能執鬼,居東海度朔山上。立桃樹下,簡閱百鬼。鬼無道理,妄為人禍,荼與鬱壘縛以盧索,執以食虎。故今縣官斬桃為人,立之戶側;畫虎之形,著之門闌。夫桃人非荼、鬱壘也,畫虎非食虎之虎也,刻畫效象(像)冀以禦凶。(東漢王充《論衡·亂龍篇》)
而立桃人葦索儋牙虎神荼鬱壘以執之。儋牙虎神荼鬱壘二神:海中有度朔之山,上有桃木蟠屈三千裏,卑枝東北有鬼門,萬鬼所出入也。神荼與鬱壘二神居其門,主閱領諸鬼。其惡害之鬼執以葦索食虎,故十二月嵗竟常以先臘之夜逐除之也,乃畫荼壘,並懸葦索於門戶,以禦凶也。(東漢蔡邕《獨斷》卷上)
自漢代而後的文獻,凡涉及此神話者,如南朝梁宗懍《荊楚歲時記》、唐李善注《文選》、五代後蜀馬鑒《續事始》、宋陳元靚《歲時廣記》……一般稱“神荼”,幾乎沒有稱“荼”者。
王充和蔡邕一再稱“神荼”,卻都沒有提到“書神荼、鬱壘之字”的事,很值得注意。是不是可以這樣推論:書字這個重要的事件,發生在漢末或漢代以後不遠的時候,漢隋之間。
還要提請格外注意的是,神荼(shen shu,音伸舒),是兩個平聲字,鬱壘(yulu,音玉律),是兩個仄聲字。“左神荼、右鬱壘”的寫法,和對聯的讀法(上聯仄聲尾,下聯平聲尾)、貼法(上在右,下在左)完全一致。與其認為是古人與今人的巧合,不如認為今人延續了古人的習慣作法。如此“規範化”了的作品,還不是對聯的始祖嗎?

四
在研究最早的對聯這一極為重大問題時,曆代古人和包括我在內的今人,都長期未能跳出一些誤區,以致產生熟視無睹的偏見。
誤區之一,隻相信有記載的、被肯定為是“對聯”的東西,少於分析研究式的探索。梁章钜之所以相信“紀文達師”之言,認為對聯產生於五代後蜀,是因為“餘慶長春”一聯屢見記載。今人多把時間推到唐代,也隻因為有唐代及後代詩論中的應對。
誠然,記載不可不信,不可不求,但決不要企望在古文獻中找出明代才有的“對聯”這個詞彙,作為立論的依據。我們必須充分注意今人研究成果,並“記載”下來,告訴後人。
誤區之二,隻承認本來意義上的“楹聯”,不大願意承認應對也是對聯的一類,仿佛古人應對的作品,算不上對聯似的。於是.盡管人們多次提及晉代已有“日下荀鳴鶴,雲間陸士龍”這樣獨立完整的、具有高超藝術價值的應對,並且在《晉書》卷二十四中找到明確的“記載”,可還是不那麼理直氣壯地說晉代已經有對聯了。
誤區之三,以為對聯一開始就要達到“完美”的程度,此後的發展,也應該“一年一個新台階”不斷有大幅度的驚人變化,而不允許最初的成果是不那麼有意識的、不那麼完善的,發展(尤其是形成)階段的某一時期也不允許發生滯緩現象。對於一種古老的文化傳統,這實在是一種苛求。麵對浩浩長江,誰能想到它的源頭竟是巴顏喀喇山中薑古迪如冰川呢?江水與冰川可是水的不同的形態呀!就對聯的長河而言,它自神荼、鬱壘發源,流入魏晉南北朝,流入隋唐,流入五代及宋(元),流向明清以至當代,奔騰而下,在時間上的連續性都能得到無數的印證。這樣,對劉孝綽兄妹“對聯”,敦煌變文“對聯”的認定與研究,便不那麼重要了,因為它們充其量也隻是一個支流。
綜上所述,就目前所能找到的資料分析,我們嚐試著得出這樣一個結論——中國對聯產生於漢隋之間,至今已有近兩千年曆史。第一副對聯是“鬱壘,神荼”,這是一副門對,相當於春聯,也是一副具有相當藝術水準的神(人)名對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