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讀俞國林先生點校的《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》,忽然想起一副曆史悠久的對聯:風聲雨聲讀書聲,聲聲入耳;家事國事天下事,事事關心。讀罷厚厚兩大本日記,深感這副對聯不僅是這部日記形象、生動的寫照,也是這部日記的作者精神世界和人生經曆形象、生動的寫照。
鄭天挺先生是著名曆史學家,北京大學教授,戰前曾長期擔任北京大學秘書長。全麵抗戰爆發後,他與學校同人困守北平四個月,後北大師生南下,他亦經天津,香港,入梧州,取道貴縣、柳州、桂林、衡陽而抵達長沙。為了繼續學業,他的五個子女則全部留在北平家中。這期間,他先後任教於長沙臨時大學和西南聯大曆史係,不久,又擔任了西南聯大總務長兼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副主任等要職,教學、研究既不輟,並主持繁雜的校務、教務等工作。

鄭天挺(左)與胡適(中),攝於1948年
(圖片來自網絡)
鄭先生的這部日記,就從他抵達長沙後的1938年1月1日開始,直到抗戰結束回到北平後的1946年7月14日結束。這些日記,其起訖時間,幾乎與西南聯大的八年堅守相始終。與我讀過的,以極簡著稱的《徐世昌日記》相比,鄭先生這部日記可謂精細而周詳,所記包括家務、親情、交友、出遊,以及大量有關校務的事件和處理措施,讀書、治學、授課、研究的細節,堪稱一部治校、治學、治生的全景記錄,亦是研治聯大曆史頗具獨特價值的史料。
這是當代中國所經曆的不同尋常的八年。對一個深具家國情懷的知識分子來說,山河破碎,國難當頭,正是他們憂國憂民、報效國家的時候。鄭先生在日記中就曾這樣表示:“平生以天下自任,當此多難之會,進不能運籌帷幄,效命疆場;退不能撫緝百姓,儲備軍實。而乃煙瘴萬裏,紀霧曉征,外蒙卻懦,內負胸臆,果何為哉?雖曰聚天下英才而教育之,以為悠遠之圖,此宿師大儒之事,又豈區區所可僭越者乎?”鄭先生的這番話是有一點悵然若失的意味在其中的。他在另一日還寫道:“自國難日急,學者好讀遺民詩文,餘則主讀中興名臣集,以為遺民詩文固可以激勵正氣,而中興名臣之所作,於激勵正氣外,兼可以振發信心。當千鈞一發之際,不有匡濟之術,烏可以複興哉?”由此亦可想見鄭先生當時迫切的報國之心與憂國之情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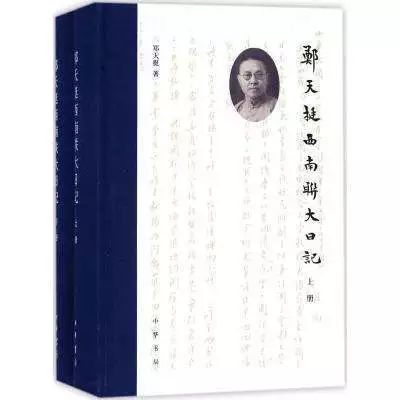
《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》
鄭天挺 著
中華書局出版
當然,作為一個學者和教師,他的家國之憂思,是要體現在學術研究和教學活動之中的。他清楚得很,抗戰建國的重任最終總要由這些學而有成的青年學子承擔起來。而囊括了中國當時最優秀的三所大學——北大、清華和南開的西南聯大,則無論師生,都是精英中的精英。所以,辦好這所大學,不僅是為抗戰凝聚精神力量,更是為了戰後建國培養、儲備人才。從日記中我們看到,鄭先生為了學校建設、教書育人,傾注了全部心血,很少有午夜十二時以前就寢的,有時上床後還要讀書一小時。他每天“入校治事”,去處理那些複雜、繁瑣的日常事務和人際糾紛,不勝其煩;但並未影響正常的教學,即使是在跑警報期間,仍然見縫插針,盡量不耽誤學生的學業。他不僅按時授課,耐心輔導,更利用晚間空閑時間,讀書、備課、命題、判卷,而且,學有心得,便作為文章,盡可能地貢獻更多的學術成果於社會。而學生中的厭學情緒,對政治活動的過分熱衷,以及對學術“無大興趣”,都讓他憂心忡忡,坐不安席,並在日記中多次提及。他很清楚,當國家麵臨生死存亡之際,大學是無法獨善其身,專注於學術的。而另一方麵,他也注意到,戰時特殊的環境,以天下為己任的時代氛圍,也為這些知識精英走出象牙塔般的書齋,融入更廣闊的社會生活創造了條件,從而引起一代學風的變化,造成一種剛健樸實的學風。
鄭天挺先生是個學者,也是個書生,在他的生命中,讀書占據十分重要的位置。早在南遷昆明之前,他就在日記中寫道:“此次南來,決意讀書,以事務相強,殊非所望。”但事實上事與願違,盡管他一再婉拒、推脫,仍然被安排了很多事務性工作。這樣一來,讀書就被擠得邊緣化了。為此,他顯得十分不安,在日記中他曾寫道:“自移居校中,終日棲棲遑遑,未讀一書,未辦一事。翻檢射獵,不足稱讀書也。工匠市儈之周旋,起居飲食之籌計,不足稱辦事也。常此以往,真成誌氣消沉之人矣。”應對的辦法,是為自己製定詳細的讀書計劃,不僅規定讀什麼書,而且規定何時讀完,每天讀多少頁。如果有一天沒有完成預定的計劃,還要找時間補上。這也是他潔身自好,律己甚嚴的一種表現。我們常常可以看到他在日記中自責,有一天他寫道:“餘自去年稚眉夫人歿,立誌不打牌,少買書,以二者夫人嚐相諷戒也。一年來牌已絕,而無用之書尚未能不購也,更記之以自警。”生活中,他的確不再做“麻將之戲”。偶然一次,因不忍掃朋友之興,“打牌竟至通宵”,他便在日記中痛責自己,上綱上線。

鄭天挺1939年留影(圖片來自網絡)
鄭天挺先生是一位曆史學家,他的日記也體現了一個曆史學家應有的嚴謹細致。無論是在長沙、桂林、蒙自、昆明,還是大理,每到一地,他都會詳細記錄當地的風土民情,生活細節,甚至定期記錄雞蛋的價格,為那個時代的日常生活保留了一份真實可信的記錄。實際上,關於物價、薪資、補貼方麵的記載,詳實而細密,是研究抗戰期間經濟史的第一手材料。其中關於日機轟炸,教授、學生跑警報的記載,包括時間、地點、方式、人物諸要素,亦是研究抗戰史的珍貴素材。這些細枝末節的記述,曆曆在目,生動有趣,讀來深為那一代學人的精神品格而感動,並心向往之。
日記中記載最多的,還是鄭先生與眾多學人的交往。梅貽琦、蔣夢麟、陳寅恪、馮友蘭、湯用彤、傅斯年、潘光旦、董作賓、陳雪屏、錢穆、姚從吾、葉企孫、賀麟、雷海宗、林徽因、金嶽霖、羅常培、聞一多、梁漱溟,等等,不勝枚舉。今日治近現代學術史、教育史、文化史者,無不可以從鄭先生的日記中得到線索,得到啟示,或可鉤沉出不少“交遊考”,以補正種種史事之不足。尤其是所記與陳寅恪的交往,為還原陳寅恪在西南聯大的生活場景提供了許多鮮活的材料。而陳寅恪在隋唐史研究方麵對他的幫助,尤讓他刻骨銘心。從這些學人的交往中,可見一代學人的心路曆程和知識分子的卓然風貌。